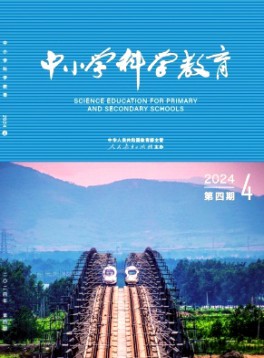-
入怀(组诗)
鸟穿蓑衣,只穿上身裙。留给了稻草人收割的,赤膊,短裤蓑草,越来越少了秋野大量堆积.鸟脱身时卸下来的碎片。
-
踏过驼峰上的黄昏
云漫漫,烟蒙蒙,驼峰山隐匿了苍茫的色块,一座山的形象和野性已殁在了迷蒙中。
-
虎崽
不好意思,讲一个故事。在故事主人公林云海的记忆里,夏庄的六月永远是美丽的,那个六月二十六的上午九点也永远镌刻在心里。如果没有英美的一番表白,他绝不会报名参军的。他属于三代单传,有个老妈需要照顾.要命...
-
焚诗(组诗)
至此曲终人散,头一遭体会到巨大静默,斧子在一边闪着冷光,更深的部分……,被相隔,被看见从来不变换墙貌,包含拒绝,最懂得是风化。
-
我的伤口
不知何时创下的伤口 不知会在哪个节点上愈合 行走的疼痛寻找良方 迷失导向的徒劳跌落空谷 我把伤口摊放在阳光下 腐恶交媾霉菌窃窃私语 轻浮裹挟傲慢肆虐无度 我把伤口裸露在手术台上 无助的呻吟牵累赢弱惶恐 撂荒...
-
漫步刘公岛
去刘公岛,天公不作美。海风呼啸、波浪滔天。最早一班轮渡,像个被大海厌弃的孤儿般,可怜巴巴地被浪涛推搡着颠簸前行。真有不畏严寒的,红彤彤的旭日明艳地从海天相连处冒出了脑袋,满脸惬意地把缕缕霞光洒向人间,不,...
-
草籽落地(组诗)
草屋 这些布局不一的草屋,比落日高一些 比槐树、杨树矮一些,再往上就是麻雀的家 鸟鸣停歇在树上,蝉呜也是 地面是天井,粮食堆在屋前的土炕上 院墙外是胡同,杂草丛生
-
垭口
春天里,我老是忆起一个小镇的一条巷子,以及在这条巷子里走来走去的一个女人。
-
大雾
模糊了起伏的山岗 朦胧了淙淙的小溪 洗亮了原创的风景 漂净了心中的尘泥
-
戴花的羊
想起亮亮的时候,我正在做爱。有人在我身下断断续续地呻吟,我捧着她潮红的脸,克制地耸动身体。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打在墙上,晃动的阴影一次次将它遮住。我抬起头,有只像蜜蜂一样的昆虫隔着玻璃看我。
-
让一粒麦子止住哭声
通知已经下达协议已经签 昨天绿渡荡漾的麦苗 今天被大量的瓦砾碎石埋住
-
赞美或者感叹(组诗)
辽阔的…… 不必提白云或者蓝天 也不用惊叹无边无际 这里,有太多的辽阔可供挥霍 从绿草织成的海洋 到牛羊铺成的大地
-
树与藤的对话(外一首)
月光下 树与藤 悄悄对话 藤说 没有你 我怎么向上爬 树说 我很开心 也有些怕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你该怎样 继续你的生涯 夕阳 山啊 请你托住 那轮滴血的太阳 别让 她坠入黑暗
-
落花
一些落花干枯着 另一些随水流走 还有一些在荒草丛中腐去 一些蚂蚁还搬动着它们
-
通往梨树林之路
我对我妈说,口渴了,想吃梨,我妈说没有,我不信,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,什么水果都没找着,在一个放碗筷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块快要融化的糖,不知道是哪天的了,不管它有没有过期,我照例剥开封皮,含在嘴里,吃起...
-
生逢其时(组诗)
那个早上,本来有许多条路让我走向鄂尔昆 这条路只是无数可能中的一种 雨后的空气橡子的气味浓得像酿酒
-
自己携了灯笼在走
十多年未能读到昕孺的散文了,此次读到颇觉感奋。
-
散章
我听见我的身体里有小草撬开冻土铁窗的声音 被醒来的二月风拧盖住…… 不要奢望物质主义大赦天下 春天是最佳的逃亡季节。 旷野中。树被追丢了衣服,风护住 蓓蕾冻红的小乳头。
-
神启猎人
先想起藏东红山脉,长毛岭河谷尽头的马鹿场。那是澜沧江上游的另一条支流,距离袖珍的类乌齐县城很远。有一条上世纪允许砍伐树木时,用于运送木材的毛石道路。路基狭窄,坑洼不平,沿着深切的沟谷,羊肠样伸向林海...
-
门
历史 这天,上午十点四十分,我从纷杂的梦中醒来。正月,怠惰着;拉开窗帘每每看到的,都是已经白炽的光。
 购物车(0)
购物车(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