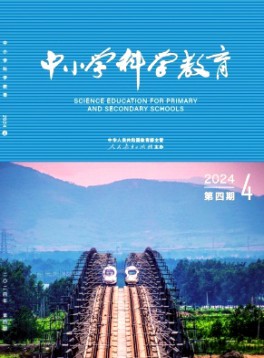-
算盘响
这个时候,郝老爷就像一摊烂泥,瘫在太师椅上。老爷那张生来就会笑的脸阴沉得吓人,一对小眼睛傻愣愣地瞪着,半天眨不下来。颌下那一撮老爷经常把玩的胡须,此时也受到了冷落,随着主人粗重的鼻息而微微颤抖。
-
云端里的昙华
一条小街 以一个瘦削的姿势 躺在昙华山的胸口 任由往来的人流仰视俯视 那一种纤细 像极了咪依噜的腰肢
-
旅程上
别丧气,夜晚即将来临, 那时我们就能秘密地看见凉爽的月亮。 存模糊的乡间上空, 我们手牵着手歇息。
-
岁岁琉璃
我想我用尽一生都学不会怎样跟不可理喻的父母相处。每每当我组织好措辞又鼓起勇气跟他们讨论些想法或打算时,收到的答复永远都是一口否决,外加一段莫名其妙的解释,尽管这些解释在任何人听来都是那么不合逻辑。“...
-
枝上枝下
枝上,是满枝腊梅;枝下,是满地瑞雪。外婆带我到佛寺参拜,我年纪尚小,并不喜欢那青灯古佛、香烛缭绕的气息,一心只想着到寺外玩雪。外婆常操着戒尺打我,让我凝神闭目,用心待佛祖,可这样的教训我只当耳旁风,...
-
刘春的诗
第三首关于父亲的诗 在某一首诗里,他曾被安排死去 也许他读过,也许没有 但我问心有愧,不止一次地 解释,写诗就像
-
沙凯歌的诗
清晨,打一盆清澈的水 清晨,打一盆清澈的水 太阳照着它,太阳是宇宙中的菊 它也会衰老,在大海的镜子里,默默死去 洗完了脸,我站在楼梯口 我在太阳下无限疲惫
-
安乔子的诗
在大地低处飞 我喜欢把翅膀低垂,沿着人间最优美的弧线 从高山到树林、花朵、浅草、蚂蚁 我渴望一一和它们亲近 大地那么忙碌,稻田和河流那么幸福
-
在旅馆
更多的人,你们在旅馆 在温暖的床上 说往日。说你们纤细的日子 你们在十月,呼吸两年前十月的空气 那时你们风一样穿过校园
-
菡子的诗
手 就这样淡淡地伸出手来 我们渴望一些什么 只觉得世界很冷 手很冷 而温暖的是远方
-
守屋子的女人
她也会走出去 到院子走走 坐一坐椅子上的阳光 许多时光 穿着长裙
-
人群中
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曾经路过你的家门 一双清澈的眼睛 凝望 门口不远处的孩群 用心灵和你交流
-
笑步吟
一这是一条被树木遮得不透光的街道,能看到事物的光好像不是从空中倒下来的,而是从两边挤进来的,或者是来来往往的车流与人流拖进来的.光到了临街的一家小店铺,更吝啬了,只洒了薄薄的一层,好像一层纱.小店铺的门半开...
-
陆辉艳的诗
南方来信:问题 乌鸦退回到夜晚,栖于枝上 成为黑夜的一部分 黑夜会因此 增添一些厚度吗?
-
飞飞的诗
我记得冬青花的味道 一个风吹着冬青树的早上 花开了,白色的一朵朵 我看不清它的样子 就像它也看不清我的样子
-
曾骞的诗
一生的答卷只有三十万 旅者在梦里推门而出 想找到 低谷里的声音 孤岛的状态
-
风瑟木美的诗
当我们老了 当我们老了,像一根枯藤缠绕着另一根枯藤 摇曳在河面上时 鱼儿一定游过来说:“看这两道阳光,多美!”
-
另一颗太阳(外五首)
我看见那么多张脸,从黑暗里生出来 火热的,如同稚气的春天 燃烧着燃烧着,慢慢的 在雨水中冷却
-
梁晓阳的诗
我是一个客死他乡的人 我喜欢这雪山,这草地,这林区,这 流水弯弯的河。在河岸村庄 有南方茶麸一样大的 馕,有盐味很足的 奶茶,有酒一样让人脸红的
-
站在一堆荒凉中间
换了三把椅子,之后,他就老了 回头想想,没有一把椅子 是他真正喜欢的。累了,实在支撑不住了 他就迷迷糊糊地坐下了。坐下了,才知 没有一把椅子是靠得住的 如今,他已经老了,用他自己的话说
 购物车(0)
购物车(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