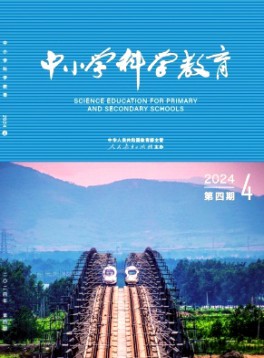-
分家
一到连阴天,张大芬心里就犯起嘀咕:这鬼天!老头子腰肌怕是招架不住吧?此时,张大芬靠在大门上,朝对面小儿子家张望。她住在大儿子家,在公路边上,是新盖的楼房。小儿子家在对面的山腰上,隔着一条河,有半里山路,说远...
-
一切都是节奏
一切都是节奏——潮汐、奔跑、呼吸山峦离低的起伏。一切都是节奏——四季、生死、昼夜、词语和语调的生成。
-
珍珠婚
和丈夫相识, 她额头的胎记只有一元银币那么大, 被一排刘海遮着,根本看不出来。 除此之外,她不存在任何的缺陷。 容貌不说闭月羞花,但也是端庄姣好的。
-
锯末山
我心事重重地走着,我这是往哪里去? 反正没有方向感,往哪里去不都是一样? 我刚才已经听小沃说了。河在头顶奔腾,这可真够刺激。 却原来锯末里头什么都有。这我可没料到。 【小说坊·短篇】
-
雉回头
槐如大伯的刨子有长有短。短的像长在秧底田里的蚱蜢,提着,随手刨掉木板上泛起的毛刺。长的则像大个的螳螂,得将木料卡在马凳上,槐如大伯弓着腰,双手捏紧长刨子的双耳朵往前推,脚也随之交替往前走,他长疣的鼻...
-
寻找余闲
余闲木然地看了看他说, 当初咱们想要的似乎都得到了,可幸福呢?不是那个事儿。 何杰文哂笑着说, 你当年不是还要在生活的柔波中打滚吗,现在不想了吧。 余闲低着头叹了口气说,我是咸鱼,这里没有海!
-
百花谷
我第一次见到吴思若是在明德四年冬天,我那年二十岁出头,可能不到,在漠北百花谷开家肉铺,杀猪宰羊。本来跟她没关系,有天快打烊的时候,有个提剑的男子跑到店里来,求我让他避一避。有人在追杀他,当然找他的人...
-
荒废的宅院
那时候,我家附近有一座荒废的宅院。院子里长满了野草,一到夏天,雨水勤,荒草长得很高,很茂盛,人都下不去脚。那里只有一座堂屋,孤零零的,门也是紧锁着的,常年没有人来,锁都锈蚀了,窗棂经风雨多年侵蚀,都...
-
春光正好的下午
地窝在被子里看书 春光正好的下午 满窗的阳光主肌肤发热 被冬天冰冻的情欲 也在此刻,因春暖而花开 丈夫就在客厅里看电视 但她没有吱声 感觉自己想要另外的爱抚
-
扎加耶夫斯基诗选
给你 这不是为你写的惟一的诗——此刻 你睡在梦织的云团里吗——哦不仅为你 写胜利的,微笑的,可爱的诗 也为你写被征服和被制服的诗
-
从乌里到乌里(7首)
在另一个年代——致艾迪特·索德格朗 透过你又大又灰的眼睛 我看见满载军队和难民的火车 穿过另一个年代的铁路 你在乡间别墅里咳嗽 老式罩衫晃动时,你的孤单
-
岛上气候
在早上的雾 下午的瓢泼大雨之后 现在是飘散的彤云 瓦蓝的天空 远山那亮丽耀眼的光,如一道 鲜艳的伤口,被一只 惊弓般跳起的鱼 看见
-
闺中密
第一次相遇,何冰热情,小茉冷淡。随着两人见面次数的增多,冷热有了消长;何冰的热度是表面的,对人的亲切不过是天性的开朗和从小的教养,而小茉却像是过桥米线的那碗鸡汤,一丝热气不出,却能烫熟菜肉。
-
烟花(8首)
烟花 我有两个想法 一个稚嫩 一个雄心勃勃的 都进人了一间 钉有“青春”标牌的 简易房子里 我再次看到它们时 他们一个一个 仿佛是一堆隔夜的烟花 而我满目讶异地望着 手里拿着过期 的情人节礼物,张了张嘴没有发声
-
时光的遗址(二首)
夜宿木鱼镇 鸟声渐稀。夜黑下来的时候,海水盖过了我的身体暖味的灯盏和欲望,伏在远处。像个偷窥者不敢发出声响。风暴来临,我们短暂,如一朵浪花或一把水沫——
-
花开的声音(八首)
败酱草 黄色的花朵 在饥饿的年代闪烁 败酱草 我曾采割你 历史的苦味 从胃的底部升到舌尖
-
复眼(11首)
沼泽 很多鸟 以及别的东西 软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泥 大教堂的钟响了三下 奶酪是天空的儿子
-
游踪(6首)
在安国寺吃茶 缓缓转动手中的茶杯 一杯禅茶 骤然穿过尘世 红尘滚滚的喧嚣
-
平衡
他用头顶着温软的草地,双肘化作身躯的支点,双脚缓缓地伸进蓝天。然后便以一种轩轩甚得的耐心,等待着阳光和阴影把他的身体雕成一棵树。
-
不来梅的黎明入门
将黎明视为源头的知识 已经在你和鹩哥之间松懈成 一种运气。比麻雀起得早 意味着你的眼睛要比野鸭的, 在威悉河的晨光中睁得更远。
 购物车(0)
购物车(0)